姜岩回应网上辩论:东方科学与文明伟大复兴(5)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13日 10:25 新浪科技 | ||||||||||||
|
第五部分 第二次科学革命是什么 人们公认,约400至500年前,第一次科学革命开始爆发。此后,多数学者认为,又相继发生了几次科学革命,哥白尼、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达尔文、爱因斯坦等等都可以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科学革命的代表。诚然,如果我们用较短的历史眼光看待,称这几次科学大进步为科学革命也不为过,但是如果我们把尺度大一些,哪怕只用1000年的尺度去衡量,
一、第二次科学革命正在到来 1、“科学的终结”是指西方科学的“终结” 第一次科学革命源自古希腊。它的指导思想是还原论。由培根首先倡导的分析和实验方法,经过伽利略等许多学者的实践与发展,以及笛卡儿从思想方法,特别是数学方法上进行的概括与总结,在牛顿那里得到发扬光大。这是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历程,它实质上是还原论的胜利。曾连任五届澳大利亚科学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学学会理事长的约翰·A·舒斯特认为:“一般来讲,科学革命发生在公元1500年至1700年之间。其间,基督教会在古代经典科学和自然哲学的基础上苦心经营而建立的中世纪的世界观不光彩的毁灭了;同时,近代科学的基本理念和组织机构在此废墟上成长起来。大家普遍认为科学革命的核心是,推翻了在大学里牢固确立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以及其附庸托勒密地心天文学系统。事实上,它们被哥白尼的天文学系统和新机械论的自然学哲学所取代了……”(约翰·A·舒斯特,《科学革命》,引自《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页835) 第一次科学革命导致了西方科学的诞生。此后的历次科学大进步都没有摆脱还原论的框架,都是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延续。不过,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后劲越来越不足,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的西方科学越来越接近其发展极限。以还原论为基础的西方科学确实出现了危机。这些危机的苗头被一些敏感的西方学者发现,极端地提出了科学已经走到了尽头,其中尤以美国约翰·霍根1996年出版的《科学的终结》一书受人关注。 霍根是《科学美国人》杂志的资深撰稿人。他在《科学的终结》这本书中宣称,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始于古人、在技术大发展的20世纪达到顶峰,历经4000年风雨的漫长求索——已经结束了。“纯粹的科学,即对有关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来自哪里的知识的探索,已进入一个报偿递减的时代。”他认为,科学是自身成功的牺牲品。天文学家已看到的宇宙与他们未来将看到的宇宙一样大。物理学家对物质性质的探索深度已与实际实验能允许的程度一样深。自达尔文于19世纪50年代提出进化论以来,生物学家已研究出最终解释大大小小所有生物的规律。 霍根在本书正文中一一将哲学、物理学、宇宙学、生物学、混沌学等近十个基础学科推向终结之后,然后在《跋》中,又把应用科学也推向终结,他认为“将来的研究已不会产生多少重大的、或革命性的新发现了,而只有渐增的收益递减。” 此书一出版,就在美国引起很大关注。据美联社1996年8月22日自纽约报道:“自然,大多数科学家并不相信霍根。但是从他们对《科学的终结》的评价来看,霍根确实言中了要害。”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托马斯·沃森研究中心的罗尔夫·兰道尔说:“我对书中的说法感到怀疑……但是很有可能是这样的。”诺贝尔奖得主、1992年出版的《终极理论之梦》一书的作者、物理学家史蒂夫·温伯格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位在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的学者说:“我并不因他而感到沮丧。我不赞同他的看法,但是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 据《中华读书报》1998年10月14日报道,这本书最早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是在1997年,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郝柏林先生为此写了一篇评论:《错把极限作终结》(郝柏林,《错把极限作终结》,《中国科学报》(即现在的《科学时报》,1997年7月18日头版)。在1998年,随着中译本的推出,这本书迅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与美国同行相比,中国的科学家们并不显得客气。在《错把极限作终结》一文中,郝柏林先生认为霍根先生一个未明言的目的,“是希望未来的科学史在讲述‘二十世纪末的哀鸣’时,提到他霍尔甘(即霍根,笔者注)的名字。”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新中国最早从事相对论研究的科学家之一刘辽先生,则用“狂妄”来形容霍根先生的野心,在涉及到相应的理论物理知识时,刘先生并未吝惜“无知”一词,但他仍认为“这是一本有趣的、略有参照价值的书。”(《中华读书报》1998年10月14日) 霍根的观点引起了很大争论,其中1998年马多克斯与霍根正面交锋的一场辩论尤为引人注目。1998年11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以《科学肯定到了终点,是这样吗?》为题刊登关于科学发展是否已经到达极限的两篇辩论文章,一篇文章的作者是《科学的终结》一书的作者,另一篇文章的作者是《还能发现什么》一书的作者马多克斯。霍根认为,科学是一个有限的领域,对它的发现可以与对地球的发现相类比,今后人类会有许多拾遗补缺的细节性发现,但不大可能出现完全意想不到的发现。马多克斯则反驳说,人类仍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和课题,科学的进取只是刚刚开始,声称这些问题无法解决仅仅反映了想象力的匮乏和广泛存在的浮躁情绪。(《科学肯定到了终点,是这样吗?》,载于美国《纽约时报》1998年11月10日) 如果我们把霍根所说的科学理解为以还原论为基础的西方经典科学,我们确实不能否认霍根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根据辩证法的基本常识,任何一种科学都有自己的特定的环境、条件、应用范围,因而也都必然具有一定的界限和局限性,走向成熟实际也就是走向终结,这种终结是必然的,比如仅仅在牛顿力学的框架内是不可能有重大的发现了,因为这些发现早已被前人完成。很多学者对霍根观点的争论往往集中在终结时间早晚的问题。正如美联社1996年8月22日自纽约的报道中所言:“没有人宣称科学将永远发展下去。有朝一日,人们将在自然、智力和技术上达到不可克服的极限。但是,由于大多数科学家看到他们各自的领域中仍存在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他们不相信科学已接近终点。”(美联社1996年8月22日纽约电) 目前,各种反对霍根观念的论述都给人以“隔靴搔痒”的感觉,要么凭自己的感情,要么凭哲学的发展观就断定霍根观念的错误。笔者认为,霍根的观念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是因为他说到了现代科学的痛处,如果把《科学的终结》一书中“科学”的定义限定为“西方科学”,那么霍根的论证是很有说服力的。笔者认为,要击中霍根观点的要害,我们必须站的更高一些。我们必须用1000年的尺度甚至2500年的尺度来看待这场争论。我们还是借用一下李约瑟先生的比喻吧。李约瑟认为,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是两列火车,公元前2世纪至16世纪,后者是超过前者的,只不过在最近400年前者蓬勃发展,暂时遮挡了后者。 如果我们把霍根所说的科学理解为以还原论思想为基础、以公理化方法为指导的西方科学,根据我们在前面所做的种种论述,确实西方科学这一火车目前出现了障碍,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出现了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 2、第二次科学革命初见端倪 如果我们用大尺度衡量刚刚过去的1000年,我们会发现这在1000年中,发生过一次科学革命并正在发生第二次科学革命。第一次科学革命开始于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其后经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和玻尔等科学巨匠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科技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构建成功了一座以还原论思想为基础、以公理化方法为指导的西方经典科学大厦,在此基础上,人类构建了辉煌的现代文明。第二次科学革命在20世纪初见端倪,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随后兴起的被称作“新三论”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以及被称作“新新三论”的分形论、超循环论和混沌论,更以磅礴的气势席卷全球,复杂科学的兴起,向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成果提出了巨大挑战。 对于第二次科学革命,一些学者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概念,一些学者虽没有明确使用这一概念,但也做了相关阐述。他们认为第二次科学革命是一场完全不同于还原论的思维革命。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1999年10月18日《科学时报》上发表《科技技术百年的回顾和展望》一文中指出:“科学面临巨大挑战与生机。不久前,一个叫约翰·霍根的美国人写了一部名为《科学的终结》的书,宣称‘伟大而又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他的调查结构从一定侧面反映了当代科学理论的局限性和人们对科学权威的迷惘。实际上,科学远没有终结,人类认识客观世纪的过程也不会停止。当代科学面临的一些理论难题,正孕育着21世纪科学飞跃的生机。”路甬祥指出:“由于客观世界的统一性、多样性和相关性,也由于科学的发展和深化,科学在继续分化的同时,更多地呈现交叉和综合的趋势。未来的科学一方面将继续沿着原有的学科结构进一步分化和深入,另一方面,则将向着综合和系统的方向发展。” 李德顺认为:“21世纪,人类已经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非常辉煌的迅猛发展的现代文明,但这个文明在20世纪末业已暴露出很多弊端,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陷入了某种困境。在这个困境面前,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值得注意的迹象或端倪。总的感觉是,人类的思维面临着一个新的大变革,即处在第二次巨大飞跃的前夜。”“现代文明思维又有三个缺陷,即抽象性、隔离性和凝固性,因此这种思维有待于突破。21世纪人类思维方式变革的趋势表现为:从实体思维到关系思维;从客体思维进入主体思维;从单向思维进入多向思维;从静态的直观思维进入动态的变革思维。”(李德顺,21世纪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趋势,《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1期,页4-9,引自页4) 吴国盛在《百年科技回眸》一文中指出:20世纪即将过去,回眸百年科技历程,我们能隐约感到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正在来临。人类正在和将要面临的变革,是一场可以与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相提并论的历史进程的大转型。(吴国盛,《百年科技回眸》,《光明日报》,1997年11月7日) 刘华杰在《论第二种科学》一文中指出:从牛顿时代算起近代科学已有300余年的历史,这段科学可称为“第一种科学”,从本世纪70年代中叶算起,科学界和思想界又在酝酿着另一种科学,我们称它为“第二种科学”,迄今它只有一个不很清楚的萌芽,至其展露头脚、结出丰硕果实,大概还需要100年时间,至其告一段落走向下一阶段,可能还需要300年。刘华杰认为,第二种科学也是理性的,是在第一种科学的基础上的发展,不是根本否定第一种科学,而是要超越它。第二种科学是“整体性的科学”,是关于复杂性的科学。目前已开始这方面的艰难探索,在国外有圣菲学派,中国有系统学学派等。对第二种科学的叫法也许不同,但实质差不多,都是在方法论上力求有发展,冲破学科壁垒,特别是化解文理科界限。第二种科学远未成熟,都不是特别正宗的“硬科学”。以非线性科学为例,它是典型的还原论科学的继续,但在发展中也不断超越还原论,目前它取得的成就首先还是第一种科学的成就,其次才是第二种科学的成就,更准确的说法是为第二种科学做准备。(刘华杰,《论第二种科学》,《中华读书报》,1998年02月11日) 目前,尚没有关于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公认定义。在他人研究基础上,笔者提出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定义如下:第二次科学革命是指目前正在兴起的、与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的第一次科学革命有着根本不同的科学革命,它的指导思想是整体论,它的研究对象是从微观、宏观到宇观各种尺度下,包括天地生人等各种层次中的整体性、非线性、复杂性、不可逆性、系统的开放性和功能性,它的持续时间可能长达几百年,它与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在第一次科学革命基础上的“扬弃”。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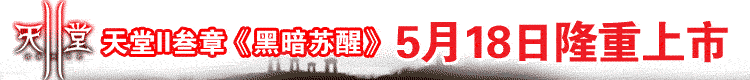
| 新浪首页 > 科技时代 > 科学探索 > 东方思维能否拯救中国科技专题 > 正文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