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进入TCL集团后,吴士宏在媒体面前公开露面的次数并不多,这对于一个曾因为“微软事件”而在IT界一度掀起轩然大波的特殊人物来说,平添了一些神秘感。无论是IBM、微软,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了,但是,在TCL她到底做了些什么?是大家所共同关心的。
天地人家:看上去很美?
记者:(下称记):你所管理的信息产业集团去年盈利情况怎么样?今年预期目标达到多少?
吴士宏(下称吴):去年总体成长从9.7亿元增至19.7亿元,在整个集团中占的比率从8%增加到11%,盈利2000多万元。今年预计增长率在80%吧,尽管要有新投入的项目,总体盈利也有增长。
记:这个“天地人家”的方案“看上去很美”,而要贯彻下去势必要涉及到改革,涉及到利益重组。
吴:我们其实是非常小心地在原来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战略布局,我们要的是革新而不是革命,革命是会尸横遍野的。
我们的战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革命,全面建设一个新的平台、新的物流系统,但是这意味着太大的风险。于是我们选择渐进、革新,找到结合的模式将电子商务和已有的巨大的网络不流血地整合起来,“天地人家”战略不是简单地把原来200多亿的生意直接搬到网上来,而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一个增量,是在原来销售网点达不到的空间里进行拓展,比如说可能是不逛商场的人。
记:目前有一个比较广泛的议论:“天”是控制在你的手上,而“地”在另外的平行公司里,那些销售队伍直接面对的是那个公司的领导,凭什么服从你这个战略布局,你有什么利益给他们?
吴:在过去一年当中,我有一个很大的工作是被接受、和基于被接受基础上的被信任,被信任基础上逐渐被理解要做的是什么事。这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我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没有必要让外界去评价,看我们最后做得成绩就是了。
记:那你们的利益怎么分配呢?吴:销售我们是不收费的,但是有一点,比如说原来是从传统销售网络上走的,现在从“亿家家”上走,前后者之间会有好几个点的成本节省,我们会在这个节省里分成一笔。但是不会说你现在把那笔钱搬到我这儿了,我就有收入了,这都是一家子里的呀!有些公司喜欢做这样的doublecredit(算两次账),我们不做这个。我们的设计是“亿家家”依靠信息家电进入千家万户,并实现增值服务,比如说针对家庭的服务、远程教育等等,在这里找到利润点。
TCL与吴士宏:谁在适应谁?
记:你无论在IBM、微软以及现在的TCL,都要经历两三个月的时间去学习,那么这个过程对于你溶入一个新的企业起到什么作用?
吴:它是必须的。
记:是你适应了TCL,还是TCL适应了你?
吴:我觉得是相互的,我适应TCL更多。我对TCL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挺明显的,但是我尽可能地留着自己的烙印,抹去自己的痕迹。我不愿意到哪就指手划脚,那太表面化。你把大的战略制定出来、布好局,形成团队去实施,整体的势态自然会表现出来。如果一开始就把精力投在一些细节规范方面,让人一看“哟,真像外企!”可那有什么用呢?所以我更多地是去适应TCL。
记:那现在是IBM的烙印多,还是微软的多?
吴:我说句大点儿的话,是比较融汇了前面的东西,和很多自己的思考和领悟,因为不可能把IBM和微软照搬过来,这就是我所谓的抹去痕迹留下烙印,这烙印当然有14年刻上去的一个一个战役、、一个一个动作,但它们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我自己的烙印。
TCL不能照搬IBM,从产业上、从历史上,从是不是国际化市场上,完全不同。更不可能照搬微软,因为这边是从一个传统产业往上砌,那边是一个全球软件行业霸主,从市场定位从文化上考虑都是不能照搬的。
记:从IBM、微软到TCL这个国有企业,你感觉它们之间的企业文化有什么不同?
吴:我是带着感激的态度进TCL的,因为它给我了这样一个选择和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至于文化上的差异,每个公司都有适合自己的选择,IBM比较讲究传帮教,微软是靠数字神经系统来管理,而TCL更灵活更自主,一定之规非常少,我喜欢这里的开放。
第二个理想:找到自己的位置?
记:你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到你的理想是把优秀的外国企业做成中国的……
吴:失败了。记:那现在是不是在实现第二个理想:把优秀的中国企业做成国际的?
吴:是。记:那你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位置了没有?
吴:当然,我想我很快就找到了。我跟你讲,我的团队是到去年5月才开始形成,因为动作晚,我要先看清楚这个企业能不能成我想成的事,我能不能融入进去?我能成多大的事?我觉得看清楚了,制定的这个战略是可以实现的。我也很高兴拥有了现在这样一个团队。
记:也就是你还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试探?
吴:我觉得应该是观察吧。
记:你在微软是这样评价自己:先是差,后是良,再是优+,那么你怎么评价自己在TCL的这段日子?
吴:我给自己一个良,某些方面是非常精彩的,有些方面是有点顾此失彼。在TCL至今,我是从未后悔,更加兴致勃勃。本报记者程小琪张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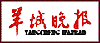
![]() 版权所有 四通利方 新浪网
版权所有 四通利方 新浪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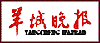
![]() 版权所有 四通利方 新浪网
版权所有 四通利方 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