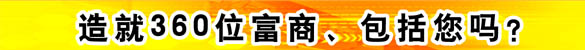专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惠根博士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04日 17:59 大连晚报 | |
|
本报特派记者刘万恒中国南极中山站电 从1984年中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登上乔治王岛,建立“向南延伸的长城”起,在20年的极地科考事业中,中国的南极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两个常年考察站傲然挺立在南极风雪中;成功登顶南极“高点”——DOMEA;巨轮雪龙号破冰斩浪,常年穿越在世界四大洋中。但是辉煌的背后,一些隐藏的问题也在日渐突出。近日,继22次科考队副领队杨惠根博士为征集科考问题专门举行了座谈会后,本报记者又对杨博士进行了深入采访,听这位常年深入科考第一线的极地考察带头人讲述他眼中的极地 项目重复、成果流失: 管理上的困难作为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著名的空间物理研究专家,杨惠根博士曾经在中国北极黄河站担任过站长,目前南极科考项目中的空间物理、地球物理部分也是他在担任总负责人。中国20年极地科考进程中,杨博士亲身参与了绝大多数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极地事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他有着感同身受的体会。 “在目前的极地科学考察组织上,我们还存在着不小的随意性,对于极地科研项目的选择更是缺乏有效的标准,由于管理的缺位,不少科研项目存在严重的重复和浪费现象。”接受记者采访时,杨博士开宗明义。他告诉记者,目前我国的极地事业重考察,轻研究;重保障,轻科学,南极 长城站的科学含量已经非常低,在本次科考中仅保留了4项科考内容,但还要常年维持一支不小的驻守队伍;即使在科考资源丰富的东南极地区,我国中山站也只设置了一些常年的常规观测项目。杨博士仍以22次南极科考为例,他说,大洋科考队的队员分别来自10多个单位,研究课题重合,缺少研究引导,低水平重复很多,仅仅关于磷虾的研究项目就有3个,“只要是研究热点就一股脑地提出申请,真正需要到南极来的科研项目却没有登上雪龙号,就算是本次考察中最令人瞩目的格罗夫山考察也是“先天不足”,在2005年5月份前连最终行进计划都没有确定,科考管理的随意性可见一斑。”杨博士认为,极地科考管理上的欠缺还体现在对考察成果的缺乏控制上。杨博士告诉记者,按照我国极地考察的有关规定,从南极采集获取的科研数据和样品,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有权分享并在解密期后进行公布。“对于南极科考这样的公益性事业来说,是没有个人私密可言的。”但在20年科考进程中,本应由国内学界共享的不少数据却悄然流失到了个人和个别单位手里,并成为绝对排他的机密。“有些科考队员回国后就不再和极地研究中心联系,所得到的数据和样本就保留在自己手里,也不按规定上交。科考头几年的不少数据是保存在5寸软盘里的,现在连5寸盘的驱动器都找不到了,但国家还是没有得到应得的科学信息。” 此外,中国极地事业的财政管理也存在一定问题。杨博士介绍说,国家的行政拨款权在 财政部,分拨给哪项极地研究事业权力在科技部和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可是南极研究收效缓慢,并不受青睐,加上还有一些诸如地磁、臭氧、电离层这样没有主管部门“娘家”,又不属于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范围内的“三无”项目,常常是数据收集回来了,研究经费却没人提供,千辛万苦采集到的宝贵信息就扔在文件袋里、电脑硬盘上,进入了长久的沉寂期。“魏文良书记常说的一句话是‘南极考察已经花了99元钱,却不肯花1元钱在研究上’,所指的就是这种现象。”杨博士表示。缺乏关注、少人问津: 人才上的断层与经济上的困难相比,杨博士认为目前我国极地科考事业面临的更明显问题是不断扩大的人才断层。“中国第7个5年计划到‘八五’期间,中科院几乎所有的地球科学方面院士都参加过南极科考。在极地考察初期,南极就如同今天的神舟飞天项目一样,被科学界看作是中国科学研究的最前沿,最热门最时髦的科技项目,吸引了大批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像秦大河院士、国内测绘界的元老鄂栋臣教授、琚宜太的老师刘小汉等都是极地学者的杰出代表。”讲起当年南极考察“群星闪耀”的盛况,杨博士津津乐道。但是随着学界热情的逐渐消退,极地科考的关注度也在一天天降低。“从“八五”以后,在南极一线工作的院士几乎没有,其他中青年专家也越来越少,中国极地事业的队伍在萎缩!”杨博士略有激动地表示。他仍以本次南极科考为例子,大洋队考察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0.3岁,最年轻的队员22岁,绝大多数人是在读研究生。而在美、澳等发达国家,南极考察者的组队年龄一般在35——42岁之间。 “队伍年轻化虽然说明我们有比较雄厚的储备力量,但毕竟说明我们生力军的欠缺,再者不少研究生毕业后根本没有留在极地研究的相关部门工作,这就造成了人才的大量流失。” 杨博士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科考条件的艰苦落后,“往返一次南极需要5个月到半年,其中航渡时间2个多月,这对于时间宝贵的科学家们是难以承受的。”其次是极地研究事业成果产出的缓慢,“科学家们是现实主义的,目前对待极地科考大多数人采取的态度非常冷静:能有成绩我就来,否则不来吃这个苦。”此外,极地事业的宣传力度和角度欠缺也是造成极地考察缺乏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海洋局有关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上,来自新华社国内部的记者张宗棠曾表示:国内媒体的关注度大多在南极这块神秘大陆本身,而并非枯燥的极地科考工作,于是媒体受众的聚焦也被分散,久而久之科考工作的关注度自然降低,吸引力也随之下降。杨惠根博士和其他一些考察队领导也比较认同这个观点。 产出缓慢、能力欠缺: 竞争中的尴尬 “也许有人认为,我们在南北极已经建设了3个常年科考站,还有一条世界闻名的破冰科考船,有这么强的极地实力,还发什么愁?”对于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乐观情绪,杨惠根认为,在21世纪后的新科技时代,在极地圈占土地,“占山为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极地科学考察的三大目的,就是权益、环境和科学。要想在南极事务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有多少考察站、有多少常年科研人员,这些硬件数字固然是衡量国家极地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世界更关注的是你在南极拿出了多少科学研究成果,而目前我们的能力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恰恰是在南极的科研产出水平一直很低。需要注意的是,在南极,最受尊重的永远是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杨博士强调说。 杨博士告诉记者, 澳大利亚的科考专家每年都要沿着南极内陆海岸线巡视各个考察站的极地环境保护工作,并提出改进建议。“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别人的指导?因为澳大利亚各站的极地环境研究成就在国际上是得到公认的。目前在南极,普遍遵守的是‘谁的成果多,谁的话声大’这个原则。各个南极大国之间存在看不见的竞争,不再是比较谁的考察站多,而是比较谁的研究成果多。”但是,由于管理机制、经费限制、人员流失等诸多原因,我国极地科考虽然收集回了大量的珍贵样本和数据,但随后进行的研究却迟迟不能开展,成果产出效率很低。“同样一项科学研究项目,我们在做,别的国家也在做,如果见效比别人慢,哪怕只晚一天得出结论,之前10年的努力也就毫无意义。科学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杨博士认为,类似的现象在物理、地质等南极项目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构筑平台、再创“热点”: 规划中的应对措施对于极地考察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国家海洋局等有关部门也在积极筹划应对措施。杨博士向记者透露说,目前极地研究中心已经成型的改进措施有以下几点:首先,尽可能多地召开有国际影响的南极科学研讨会议,扩大极地研究的圈子,吸引更多相关学科的著名专家了解南极,到南极来,把极地考察再次打造成中国科学界的新“热点”。其次,修炼“内功”,继续完善自己的科考能力,为科学家们提供先进的研究平台和运输平台,进一步完善数据和样本共享机制,目前由财政部和国家海洋局牵头建设的极地样品库正在筹划立项之中。此外,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还在积极筹划以中心为龙头,联合海洋局三所、国家测绘局、中国科技大学等极地环境研究机构,共同建设以网络为平台的“虚拟实验室”。“如果这个实验室建设完成,可以成为我国极地研究的联合舰队,必将大幅度提升我国的极地科学研究攻关能力,改善我们的研究产出效率。”杨惠根最后总结说。 (每日内陆队动态)格罗夫山考察队陨石收集工作进展顺利,目前已收集到17块陨石,作业环境零下24度,白化天气已经消失,内陆队队员表示4日将从1号营地起程继续挺进内陆猎取陨石本报特派记者刘万恒中国南极中山站电北京时间1月4日凌晨1时,内陆考察队队长琚宜太在每日向中山站的例行汇报中报告说,目前内陆队克服了低温、白化天等恶劣气候的影响,目前陨石收集工作进展顺利,已收集到17块各种陨石。 琚宜太在电话中汇报说,从1月1日晚间开始的白化天气到2日深夜已经消散,但格罗夫山一号营地所在区域的气温仍然很低,目前在零下24度左右,且风力强劲。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11名内陆队员还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克服天气影响,全面开展了陨石收集工作。琚宜太激动地报告说,目前内陆队已经累计收集到17块各型陨石,在开展工作短短几日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这在历次内陆科考中也是不多见的。 琚宜太还通过电话告诉记者,目前内陆队的3号雪地车驱动轮在风雪中发生了断裂,这虽然对队伍行进没有根本性影响,但还是会影响到行进速度,目前全队正在抢修雪地车,并希望领队魏文良返回中山站后能给内陆队送去维修配件。琚宜太表示,内陆队将于1月4日起程,提前离开1号营地,前往下一个作业地点展开工作,以躲避1号营地附近持续不断的暴风雪。 |
| ||||||||||||||||||||||||||||||||||||||||||
| 新浪首页 > 科技时代 > 科学探索 > 中国第22次南极科学考察专题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