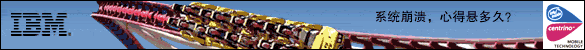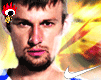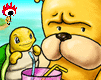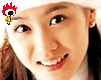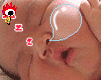| 《中国科学探险》:金三角--谁的后鸦片时代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14日 16:10 《中国科学探险》 | |||||||||
|
撰文\摄影 韩云峰 从罂粟到鸦片到吗啡到海洛因,人类在100多年以来迅速将这种美丽植物中蕴涵的邪恶力量提升到了极至。 这块交织着血腥与蒙昧的土地上,大规模移民和替代作物的种植真的能显出改变现
2004年春节前后,我们的吉普车行驶在缅甸东北部的山路上。 5年前,金三角地区最重要的民族武装佤邦联军的司令鲍有祥将大约6万佤邦烟民从佤邦北部辖区搬迁到南部辖区,那里的气候条件无法种植和收获鸦片,所以佤邦移民将不再从事罂粟种植——这种备受谴责却获利菲薄的营生。鲍司令向世界许诺:2005年佤邦将告别鸦片。 鸦片时代的牧歌 在中老边界有个叫“尚勇”的地方,是属于中国云南勐腊县的一个乡。从尚勇乡向南越过边界是老挝乌多孟省的那莫县。我偶然认识了两个极其普通的边民:岩仑和岩卖,是一对表兄弟,一个住在尚勇,种甘蔗为生;另一个住在那莫,除了种旱田,也种鸦片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正是他们两个,引发了我进入金三角地区的欲望。 1998年岩卖第一次带我去他的罂粟地的时候,我只看见一个憨厚的农民在温润的土地上慢慢地耕作,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们与“金三角”或者“毒品”这些词联系起来。岩卖夫妇到自家的罂粟地需要走几公里的山路,过两条河、过三道山。因为老挝政府出台的政策不允许在大路边种鸦片,所以他们只好把地开在雨林深处。收大烟的时候,孩子们也常常学着岩卖的样子,耳濡目染,等他们长到五、六岁的时候,就可以成为收割鸦片的行家了。 收割鸦片是一项疲乏不堪、累断人脊背的工作,需要经验和熟练的技巧,几个世纪以来,收割鸦片的方法几乎没有改变。工具通常是一把专用的刀,由一系列3个或4个平行的刀片组成,用这种刀在罂粟蒴果上切下垂直的刀口来采集蒴果里的鸦片汁液。刀口不能太深,那样会使汁液流得太快而滴到地上浪费;当然也不能太浅,否则汁液流出太慢会粘合切口而成一个痂。理想的深度是1-1.5毫米。 “上山为了采花,下山为了讨饭,满山的洋烟花开了,那就是钱来了呦,外出的亲人你在哪里呦,还不如在家种洋烟。”总是在9、10月份雨季过后,岩卖唱着古老的歌谣开始播种罂粟。大烟籽是灰白相间的,像芝麻那么大。他把籽装在书包里或者干脆拿破布一兜,然后每次用三个手指捏一点出来均匀的洒,洒完后用锄头把地翻一下,籽就埋在土里了。罂粟被他们称作“懒庄稼”,用不着特别精心地管理,翻了地之后就不用管了。 老挝北部与中国交界地带的烟农差不多都是跨境而居,没有国界的概念,他们像岩卖一样温顺憨厚,很多人似乎还处于半蒙昧状态。有一次岩卖带我到一户罂粟种植者家里,他们留我在家里吃住。因为人比较多,就用一个大盆盛饭。晚上他家殷勤地给我端水洗脚,水盆正是在中午用来盛饭的那个。 老挝北部的罂粟种植者主要是大山深处的苗族。他们在二战前后被法国殖民者一半引诱一半强迫着开始了罂粟种植。与之相对称的是在边境另一侧的缅甸北部的掸邦高原,当英国的势力在更早的时候触及到湄公河与萨尔温江之间的肥沃土壤时,他们立刻发现掸邦高原与印度(殖民时代最早的大型鸦片种植基地)的地理气候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两股殖民势力终于在湄公河两岸的历史画卷中隔岸相望,罂粟花渐次开放在两侧海拔800-1200米的山坡上。 掸邦高原种植鸦片的主要是这里的佤族,烟农家里的床上几乎都备有烟枪。许多家庭的早晨是这样开始的:幼小的孩子还在沉沉地睡着。长辈们已经醒了,但是并不急于起来,其中的一个则手拿起烟枪——里面装着鸦片,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根长针,把盛着鸦片的烟枪烤在烟灯上等待鸦片溶化。当鸦片逐渐汽化,这时,他(她)会深深地吸上一口,然后一边抽一边用针捅进烟锅保持气孔通畅。烟雾从鼻孔缓缓地呼出,抽烟者则极为专著地抽吸和享受着,然后自己也沉沉睡去……在这个上午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她)都将沉浸在一种沉静却萎靡的状态里。 烟农把所有从罂粟身上收获的东西都拿到市场上去卖:罂粟苗可以当菜吃,罂粟籽可以榨油也可以磨成“豆浆”喝,罂粟杆可以喂牲口……最壮观的当然还是卖大烟。在掸邦的营盘镇,成千的人在一起买卖大烟,车马错杂、人声鼎沸。虽然那是毒品,但在当地人看来,那是土特产。 鸦片交易里使用的主要是人民币和100多年前英属印度币——当地人称“英国老盾”,一枚“老盾”大概相当于27元人民币,当地人用惯了它,喜欢要“老盾”。买卖鸦片的人也是自成体系,有好几种人:第一个是田间地头的交易,那是些最初级的毒品贩子;另一种是带着钱和货到村子里去交易;更厉害一点的就是去赶烟会的——被称为“坐户”,是专业做鸦片买卖的,他们往往带着本金来到烟会——拎个大皮包,里面有四、五十万人民币现金,一个季度下来(利润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大),能赚到七、八万;还有一种是做鸦片期货的,比如计算一个村子有多少户能种多少大烟,可以在收获之前提前买断,如果遇上天灾人祸收成不好,那期货商就倒霉——但是风险大,利润自然也大。 最初穿行在热闹的烟会或是坠满划开的罂粟蒴果的田间,有时会受到鸦片的影响,可能是头晕、还可能会轻微的恶心。记忆中鸦片或者罂粟花弥漫在空气里,总是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这种味道甚至能帮助一些烟农判断时令:当他们在早春的清晨起来时头疼恶心,他们往往会立刻知道:收获季节已经来临。 鸦片从罂粟蒴果里刚流出来时是像奶一样乳白的颜色,等它凝固住就变成浅褐色,然后时间越长就变得越黑,一直黑到沥青那样——这很像是一个寓言:当鸦片在烟农手中生产出来的时候,和其他农业产品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但从烟农手中卖出之后,随着毒品的提纯和利益的激增,交易的颜色也逐渐变“黑”。 金三角的三国演义 如果说金三角的边民与世无争的生息劳作给人一种田园牧歌的宁静,阅读金三角的历史却像是掀开了一口沸腾的热锅。一百多年以来,在金三角地区(特别是缅甸北部的掸邦)一直分布着如此众多的民族武装,他们不断互相开战、又不断缔结和约、而且不知疲倦地撕毁和约以及重归于好;同时,也不忘记对政府军施以攻击。 很多人相信,混乱的深层原因除了民族矛盾,不乏来自英法殖民者为当地启动的畸形的“鸦片经济”。而美国发动的越南战场又为金三角的“鸦片经济”上足了发条。“鸦片戕害的美国大兵远比在越南稻田里军事行动中丧生的为多。”美国传媒这样评价。不仅如此,很多美国士兵成为金三角、曼谷和美国之间海洛因运输的使者。麦科伊的《东南亚的海洛因政治》更是揭开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越南战争中卷入金三角毒品贸易的黑幕。 对于20世纪70年代外部势力对金三角的觊觎,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布司是这样描述的:“国民党对缅甸的混乱颇为满意,这可以使自己的鸦片收购商在掸邦的活动通行无阻;中央情报局也同样满意,这样可以使它浑水摸鱼地进入中国收集情报;而泰国一直是缅甸的死敌,它当然乐于向各种叛军提供枪械,使之成为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带……” 1999年4月17日,当我来到佤邦的首府康邦,那些经常被国际传媒演绎的所谓“金三角毒枭争霸战”的主角们正纷纷在会场里微笑着寒暄落座。1989年佤邦联合军拥兵进驻康邦以来,缅甸北部的鸦片高原——掸邦逐渐平息了战火,4支主要的武装力量控制缅甸北部4个高度自治的特区。群龙聚首是为了庆祝进入和平建设时期10周年,同时大家纷纷声明要为金三角全力禁毒。 金三角地区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佤邦联合军的司令鲍有祥端坐在主席台中央。他从16岁组织自己的军队开始,和金三角其他武装力量的首领一样,也是在战争和毒品贸易中建立起自己的王国。鲍有祥爱用“统一”这个词,据说在16岁的时候他一个星期打一个寨子,直到把昆马(他的家乡)周围所有的寨子都“打下来”。 鲍有祥承诺2005年佤邦辖区将成为“无毒区”。我拜访他的时候曾经问他:“如果国际社会不给你足够的援助,是否会动摇佤邦的禁毒计划?”他说:“禁毒工作我们早就有计划。我们在政治上受到的国际压力太大了。靠种毒品求生存,我们不能再走这条路了,要另外寻一条路走。我们动员老百姓种经济作物,并且从交通、能源上也做了一些努力:过去佤邦没有电站,现在我们搞了四个10000多千瓦的电站。这些基础设施就算具备了。另外,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我们可以进中国做生意了——当然,不是毒品生意。” 对于鲍司令的承诺是否将会实现,很多人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一些人怀疑,“毒品替代不是以正常的经济活动来替代罂粟种植,而是根据国际毒品市场需求的变化以人工合成毒品生产替代鸦片和海洛因生产”。但是无论如何,更多的人相信,打击和封闭将不会成为国际社会面对金三角的态度方式,因为那将只会带来消极的结果。 移民的后鸦片时代 鲍司令把大约6万佤邦烟农从佤邦北部辖区搬迁到南部辖区,据说那里的气候条件将无法种植和收获鸦片,佤邦移民将不再从事罂粟种植。 移民是在1999年开始的,当时我正在佤邦。移民之前,佤邦军先在“孟嘎农业开发区”做了一个移民实验,把山上的老百姓移民到山下海拔300-400米的平坝,但是遇到了不小的问题——疟疾。平坝原来住的都是花腰傣,他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即使被蚊子咬了也问题不大。但是山上下来的佤族人甚至可能都没见过蚊子。而且当时也没有药。移民500人,死难200人。我当时进入那个村庄之前,在朋友的建议下先打了预防的疫苗。 走进这个村落的时候,整个村子安静得很。在一个玩耍的儿童旁边,另一个更小的孩子一动不动地躺在他身边,一只苍蝇飞上他一动不动的额头,那个幼小的孩子却没有任何反应。而大一些的那个孩子看也不看他的弟弟,只是盯着我手中的相机。突然,他的弟弟摇了摇头醒了。我舒了一口气,原来他是活的。 真正大规模的移民随后开始。在一个刚刚进入收割的罂粟地里,一个妇女收割的时候,忽然被人喊走了。很多人被士兵带上了车,一些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有的人在哭,有的人很愤怒,但是更多的人只有听从。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将要去的那个地方究竟在哪,很多人说“是去泰国”,因为南部辖区在泰国和缅甸交界的地方。佤邦政府还是很负责的,给老百姓打针预防,也有医疗队。我记得当时的移民车辆在山谷和山坡之间,排成了长长的队伍绵延了数十公里。 2004年,我们在鲍有祥的首肯之下,乘车向南部辖区前进。从佤邦联军的北部辖区到南部辖区之间的地盘不属于佤邦控制,为了前往南部辖区,我们必须穿越崇山峻岭,经过20多道关卡。在大山深处目前有30多个大大小小的民族武装盘踞,其中多数仍然在生产和贩卖毒品。一路保护我的佤邦联军士兵始终紧握长枪。 南部辖区的人现在都改种植农作物了。我们遇到一个村长叫老八,我问他:“这些人你都怎么管啊?”他说:“你不知道,这些人刚来的时候好多都吸毒,而且以为是叫他们过来做毒品生意的,到这来一看给他们发锄头让他们干活,那哪干啊?不开田,我说:我提醒你们三遍,第三遍还不改我就抓人了。这里的田随便开,谁开下来,田就是你的了。有那么几户,来了以后好吃懒做不干活。第三次,我带着两个兵,去了就拿脚镣夹上让他们干活去,后面还有士兵拿着刺刀。把田开完了,再除脚镣。” 移民里还有一些从中国请去的农民,目的是给这里的佤族做劳动榜样,李三就是其中之一。“好多佤族人不愿意下田,他们认为脚踩水田会生病。”李三告诉我,“所以第一年都是我们中国人带着他们,种出来之后粮食堆满仓,佤族人就呆不住了,说:我们也得学。结果第二年、第三年中国人就种不过佤族的了,因为他们有力气。”我问李三:“那你们有没有生疟疾?死人了吗?”他回忆,这个村子的中国人经常被叫去抬死尸,“后来抬都抬不动了。所有6万移民,据说一共死了将近2000人,但我估计可能还多。” 其实南部辖区的气候的确相当优越,在这里,那些活下来的人不仅戒掉了鸦片,还享受到一年种的粮食可以吃两年、粮食堆满仓的日子。那些以往被穷困和鸦片围绕的佤族人第一次在自己家的房檐上挂上了满满的玉米。 无数国际传媒都在指责佤邦联军的移民没有人权,但是我得承认,在这块饱受鸦片浸淫的土地上,这些用千百生命换来的微薄的温馨瞬间——那些不同于往昔的佤族人自信的微笑、那些开始充实起来的房檐——使我多少见到了金三角未来的希望。 |
| 新浪首页 > 科技时代 > 科学探索 > 科普杂志封面秀专题 > 正文 |
|
| |||||||||||
|
|
科技时代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48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