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D-SCDMA(时分双工同步码分多址)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这两年来,众多媒体一直津津乐道。作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TD-SCDMA标准于2000年5月在土耳其召开的国际电信联盟(ITU)会议上正式通过,与WCDMA和CDMA2000并列为第三代移动通信世界三大主流标准之一。这是百年来我国电信技术史上的重大突破。
由于拥有TD-SCDMA的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可望在建设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中节约近千亿资金。并可以凭借国内市场,用这项技术来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一改近几年我国移动通信运营业蓬勃发展,而制造业却举步维艰的局面。它的主持制定者就是被国内外通信界人士称为“中国第三代移动电话之父”和“TD-SCDMA总设计师”的李世鹤。
记者是在采写有关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的文章时,才知道李世鹤的。但他在业内早已声名斐然。
作为改革开放后邮电系统中第一个学成归国的博士,他曾发表专著两部、论文七十余篇,获国内外专利十项。
但自称工程师的李世鹤更注重成果的实际应用,即产业化。1985年,他为重庆主持了第一个蜂窝移动通信网的设计和设备选型,该通信网已于1987年开通使用。1992年,组织开发成功我国第一台移动通信手持机,为国家填补了空白,使进口手持机的价格有所下降。1998年,其组织研究开发的SCDMA无线接入系统,是国际上第一个使用智能天线、同步CDMA和用软件无线电技术实现的通信系统,作为国家重点推广项目,广泛使用于国内通信网。
当然最出名的是其担任总设计师的TD-SCDMA。目前李世鹤正承担着组织开发全套TD-SCDMA系统设备样机的任务,这将是国际上最具有竞争力的第三代移动通信设备之一。
虽然是个成功者,但李世鹤同时又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他的思维总是超前,“不合时宜”:20世纪60年代,视循规蹈矩为理所当然时,研究生毕业的李世鹤刚参加工作,就一门心思地搞创新;80年代中期,中国将移动通信看作是贵族用品、警察抓小偷的玩艺儿时,他又力主发展并投身移动通信领域;在举国上下都热衷于跟踪国际先进技术时,他偏要想怎样才能超过。
他的直率和不会妥协,也不是每个领导都能容忍的:敢跟部长、院长拍桌子;在担任国家“863计划”个人通信专家组组长时,他当着科委主任的面,指摘“863”的宗旨及实施办法;为了能够实施科技产业化,他甚至几次辞掉领导出于器重他而委予的官职。
但他的老同事、部下和学生却喜欢他:淡泊名利,讲义气;思想活跃,有魄力;心胸开阔,学风好。他的夫人林敏和他带的第一个研究生、跟随了他16年、现为TD-SCDMA项目开发部主任的李军,不约而同地给他下了记者印象最深的评语:“他是真正的男子汉”。
同时不少人替李世鹤抱屈:如果这项标准是在欧美提出,他将会名利双收,甚至像CDMA技术的发明者一样当个首席执行官。 实际上,就是大唐电信奖励他的5万元,也被李世鹤捐献出来。
记者为写这篇文章三赴大唐、两访李世鹤,形成这样一个印象:如果李世鹤是个计较名利和个人得失的人,出国前才摘掉反革命帽子的他,1983年不会谢绝国外公司年薪四万美元的聘请毅然回国;当然更不会有今天TD-SCDMA的出现。
当年,作为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历史上最短时间内拿到博士学位的人,李世鹤在他那篇被学校展览的博士论文的第一页上写道:“献给我的祖国。”
今天,即将退休的李世鹤说:“我最满意的是,当我六十岁的时候,终于做了一件对中国有贡献的事情。”名家专访
我国一直在提跟踪国际先进水平,但我研究技术,跟着跟着就不想跟了,推出TD-SCDMA就是为了超过美国高通的CDMA
记者:您是怎么想起来要推出TD-SCDMA?
李世鹤:说实话不是我想起来要搞的。我认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1993年,美国高通公司提出了关于移动通信的新体制CDMA,我也在研究、跟踪、掌握这个技术。到了1994年,思路就清晰了——现在的国家863计划,都是讲跟踪国际先进水平——我研究技术,跟着跟着,就不想跟了,这个时候就想怎么才能超过他们。当时正好有两个比我小得多的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留学生,到北京来找到我。就谈干什么,怎么干。那是1994年的夏天,我刚调到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前身)当副院长,谈了两天谈出兴头了,干脆就不上班了,关在一个房间里面连谈了三天,就是放开谈。那时候还没想到TD-SCDMA,就想用CDMA的原理,采用哪些国际上最新技术超过高通。那三天谈下来,就把这五六年发展的技术脉络理清楚了。我们连一个文字都没有记,不愿意记,脑袋就够了。
我们认识到光谈不行,要做。就组织了一支队伍。1995年的春天,我带了一个小组到美国去考察,当时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现大唐电信董事长周寰也在美国,我们约好就在美国碰面。我们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租了一间教室,又讨论了三四天,最后决定干。周寰的魄力和远见在这个技术的成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干什么?名字取好了,叫做SCDMA,就是要超过CDMA。要采用的新技术在当时是根本不成熟的。于是就鼓励在美国的朋友成立一个公司,让他们和我们研究院成立一个合资企业,专攻这个技术。1995年11月合资公司运转起来。当时在美国干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我们天天进行调查,怕我们偷了美国的什么机密技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真正成型,1997年通过了国家鉴定(2000年获国家科委一等奖),到1998年才形成了可以称得上是第三代的标准,取了TD-SCDMA的名字。
但是这时候那两位在美国的朋友却感到:你干的事太有风险,不敢跟着走,才剩下我带着这批学生队伍(以大唐电信研究生部毕业生为骨干)前进。他们就不相信TD-SCDMA能够成功。
TD-SCDMA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会得到运用,这是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
记者:为什么他们不相信能够成功,而您正好相反,并且事实证明了您的判断是正确的?
李世鹤:为什么他们不相信?他们讲了,从根本上讲,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有许多非技术因素。因为中国是一个穷国,从来都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你要提出一个国际标准来,发达国家的公司首先是不相信,接着很快就要将它卡死。这是非技术因素。1998年6月国内审查已通过,我们就要向国际电联(ITU)提交文稿了,这时候有家极力想推动我国跟着他们走的日本厂商,打电话给我们的运营商:“我们听到一个谣言,中国也要提一个标准”。但我们这个“谣言”已经马上要发出去了。而且,这是一个要耗费上亿元投资才能做出来的东西,做不出来呢,即使成为标准也等于一张废纸。如果哪一环过不了也就等于白干。美国的朋友认为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值得。我却相信会通过。
第一,技术上没问题。我分析了美国、日本他们提出来的标准,我们的肯定比他们的先进。去年10月底我去参加ITU的会议,我根本没有说话,美国代表团提交的移动通信发展方向的提案,实际上在说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TD-SCDMA。我们比他们早看到了几年,技术上的判断我敢说我有的。
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国家这张牌。中国虽然是一个穷国,但毕竟已改革开放二十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哪个外国制造商在中国面前都得老实一点。我们经常打中国政府和运营商这张牌。我们的政府和运营公司对中国自己的标准是非常支持的。他们说你的技术我不十分清楚,你的产品更是没见到,但是我要在国际上叫喊支持你。没有这些因素是不行的。
第三,只要下定决心,我相信没有办不成的事。所以三年来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当然现在还得要咬牙将事情做完。
记者:您感到TD-SCDMA在中国肯定能够投入商用?
李世鹤: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会得到运用。这是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你的好东西,比别人走得远,当时别人不懂。第一步就想把它杀掉,就是置之不理;等明白拿也拿不掉了,那时才真正研究这个东西。研究后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感兴趣:二是在鸡蛋里再挑两根骨头,在市场竞争上卡我们。
WCDMA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搞了多少年,结果到现在发现了一大堆技术上的问题,也没能形成产业。有人讲我们是后来者的胜利。对了,我们在整个产品、市场推广上可能还要比国外公司晚一年半年,但是任何技术都有一个起始时期,一年半年算不了什么,我们很快就会赶上去,那时候许多厂家可能会感到用我们的TD-SCDMA更好,怎么会打不开市场呢?现在要跟我们合作的厂家已经排上队了,独立开发这项技术的厂家也有好几个。
记者:现在有人担心,TD-SCDMA本身是好的,但是至于产品,以中国现有的工艺水平是否能造出来?什么时候能看到成品?
李世鹤:我认为这个问题得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我们这次根本不是走原来国内研究开发的路,设计方案是我们和西门子公司共同做的;制造找的是德国专做小批量样机生产的公司,他们根据图纸制造,再将形成生产的全套工艺交给我们,一个月后TD-SCDMA系统的商用设备就会出现。今后的生产将在上海大唐和上海西门子共同进行。
另一方面,我哪怕不做产品,谁做就让他们交钱。就像外国公司原来对我们一样。原经贸委一个司长告诉我,这些年来我国每年在通信产品上交出的技术提成费超过一百亿;现在反过来,我们起码要它们交回一二十个亿。
记者:您能预测一下它的前景?
李世鹤:我是很乐观的,三年以后哪个厂商占老大、占老二我不知道,但这个标准本身,肯定会形成上百亿、搞得好上千亿的产业,当然不光是中国制造商、也包括外国制造商。
我倡导学生们跟我争论,不喜欢亦步亦趋跟着老师的学生。年轻人有志于搞技术,就要创造,哪怕错了也没关系,只要不停地创造就有可能成功
记者:通信行业比较尖端,您年近六旬为什么还能够站在前列?
李世鹤:正该六十岁的时候站在前面。三十、四十岁站不到前面,那时的知识差远了。
记者:有人统计过,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年龄多在三十多岁。
李世鹤:那是在一个点上——通信方面只有两个人得过诺贝尔奖:一个是发明信息论的,那个人是数学家,对通信一窍不通;另一个是物理学家,他发明了半导体,也不是搞通信的。真正搞通信的一个也没有。因为通信是集体的智慧,绝不会一个人搞成——年轻人可以在一个点上突破,在一个面上是做不到的,那需要花很多默默无闻的时间进去。年轻时在某个技术领域钻得很深了,除继续当教授外,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当了老板,比如比尔.盖茨。另一条路是当工程师,如高通的总裁,他是CDMA的发明者。我对自己的评价一直是一个工程师。工程师要求的是一个系统性的知识,我做的事是把很多人的成绩加在一起。
记者:您为什么能够成为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历史上在最短时间内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在校期间又发表了多篇论文?
李世鹤:我的基础比外国学生要雄厚。我在南京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上学时,在高等数学和物理上下了很大功夫,以后这帮我很大的忙。新东西没什么,别人达到了十,你在前人基础上提高就达到了十一。如我搞的智能天线,就是从美国雷达那里得到了启发,将它移植到通讯中。
记者:您的一位老同事说,您刚参加工作时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创新意识,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如果年轻人有志于取得您这样的成就,应该怎么办?
李世鹤:得承认每个人的智力、能力有差距。但主要得益于我的老师的指导。我大学毕业后做了当时很少有的一个选择,从工科大学毕业,去当理科研究生。当时学得很苦,教授要求很高,但我在创新的学风熏陶下,掌握了好的科研方法,相比之下,有些大学的学风就是亦步亦趋,缺少创造性。我刚参加工作时,原邮电部第四研究所出了个笑话:60年代,我们亦步亦趋学苏联,以致于前苏联的机器运过来,上面有一个坑,我们造出同样的机器后,就为如何也仿造出这样一个坑而伤脑筋。一位有自己头脑的技师看后,就拿榔头在相同的位置上敲了一下,因为那个坑原本是搬运过程中被砸出来的。所以我现在用人主要不看这个人聪明不聪明,而看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比如清华大学的学生大都有自己的头脑,想搞自己的一套,哪怕他的想法是可笑的。我倡导学生们跟我争论,不喜欢亦步亦趋跟着老师的学生。年轻人有志于搞技术,就要创造,哪怕错了也没关系,只要不停地创造就有可能成功。
我认为国家实施“863计划”要有所不为、有所为,采用资本运作,按照投入-发展-卖掉-再投入的方式
记者:您1992-1994年担任国家“863计划”个人通信专家组组长期间,负责开发成功CDCT(中国数字无绳电话)系统,填补了该项目的国内空白。但您却认为“863计划”运作模式应该改变,为什么?您认为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应该怎样搞?
李世鹤:我搞的那个系统参加过展览会就完了。“863计划”实施多年来,我们的科研成果一大堆,奖状一大堆,为什么中国的高科技市场却是老外的?就是因为想着要用一点点钱、一点点时间拿出国际水平的成果,那么你什么时候能够形成高技术的产品、高技术的产业?现在的科研资金就像是洒花椒面,什么项目都上,结果每个项目分得的经费很少。国家投入的科研经费每年在一百亿以上,如果将其变为投资、股份或风险资金,这样滚雪球式发展下来,现在可能一年已有几百亿。因此,我认为国家实施“863计划”要有所不为、有所为,支持时采用资本运作,按照投入-发展-卖掉-再投入的方式。1994年,我在科委会上谈到这些观点时,不少地方科委主任表示有同感。
我在硅谷的时候遇到国内的朋友,他们都很担心,怕我们与台湾相比,有丧失高科技优势的可能。台湾在硅谷搞高科技,以民间的名义来投资,起步的时候只有几亿美元,现在已经达到上百亿了。他们将美国硅谷的技术,通过投资拿到手,带回台湾。
“863”的运作模式非改变不可。
TD-SCDMA不可能由民办企业做成,现在我们做的事已经超出了一个企业的能力范围,已经是国家行为
记者:您早就感到在国营研究院体制下干事不顺,现在更这样认为,为什么?
李世鹤:关键在于整个模式不是企业化运作,不是从企业角度考虑问题。我们搞TD-SCDMA的开发,做过计划,从1999年开始到2001年两年半的时间,需要五个亿人民币。西门子同期会投两亿美元。我们的困难是,虽然这项计划已被批准,但是每用一笔钱,都要上级审批,不能及时得到。我们现在的研发队伍有二百多人,新的成员招不上来。
记者:为何不以TD-SCDMA的名义创办一个公司,独立运作?此前已有中科院计算机所成立联想公司的先例。
李世鹤:中科院计算机所领导开明,了不起。联想从计算机所独立出来,反过来将计算机所吃掉,国家资产增值百倍以上,是典型成功的例子。
去年我们TD-SCDMA开发部与北京风险投资公司谈了一两个月,投资公司愿意投资我们开发部,并保证此投资在三年内增值一百倍,即现在只有50、60亿元人民币价值的大唐,将拥有一个价值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高科技公司,中国现在还没有价值这么大的企业。如果合作成功,我们的项目马上能得到上亿美元开发经费,这样工作条件会得到很大的改善,技术人员还能拥有股份,这就成了他们自己的事业。但由于种种原因,大唐没有批准此项合作。
现在大家也在想办法,寻找其他的合作伙伴。
记者:有人讲您如果有好的环境和条件,会作出更大的贡献。您的看法呢?
李世鹤:很难讲。TD-SCDMA没有大唐、信息产业部的无形条件作后盾,很难做出来。我个人没有多大能耐。TD-SCDMA不可能由民办企业做成,现在我们做的事已经超出了一个企业的能力范围,已经是国家行为。到最后非常明显,TD-SCDMA标准通不过、产品做不出来,是给国家丢脸,现在必须有国家明确的支持,而大唐可以得到这样的支持。当然它的运作方式有好多我不赞成,包括有些领导对我是又不高兴又害怕,说这个老头不讲道理。但是从标准到样机的出来,没有依靠国家这一根本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无形的条件,是根本不可能成功。
既然已得到了一些东西就得面对另一些不如意:如体制方面、官僚机构,当然要做一些妥协。关键就是你到底想不想让它成功?你投靠国外公司是否一定就能成功?
至于以后产业化做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说实话,那也不是我关心的问题。只要能把技术全部做出来、贡献出来,让其他任何人接着去做都行。
中国是有缺点,但欧美国家我也走得多了,去过之后我感到很满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终于给了我们为自己国家干事的机会
记者: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李世鹤:印象深刻的事不是很多。那时在大学里吃不饱肚子,我早晨天天起来读英文的时候,就是感到没饭吃。当时《中国青年》上一篇文章给我的印象很深,叫“冼星海在巴黎”,冼星海在比赛中得了第一,他要求得到的奖励是饭票。我把它抄在了当时的日记上,“文革”中这成了我很大的一个罪状:个人主义思想极其严重。说实话我是从大学之后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小时候就知道玩儿。
记者:为什么?
李世鹤:跟困难时期有关系。当时中国实在太穷了,穷得连饭都没得吃。那时候前苏联为什么要整我们,不就是因为我们贫困,缺少技术?那时候许多人都饿肚子,有的人沉沦下去了,有的人振作起来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基本上没有轻松过。
记者:您的同事认为您的思维方式好像与一般的老知识分子不一样,并分析说可能是因为您出过国,接受了国外的思维方式。
李世鹤:可能是不太一样。非常明显的一点感觉,就是我与他们谈话要考虑半天,得谨慎。但院里出过国的人很多,这不是主要原因,我跟美国回来的留学生思维方式也不一样。
记者:差别在哪儿?
李世鹤:特别是年轻的留学生,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想怎么能够把自己卖掉。我只想着怎么能做成一件事,至于个人能得多少……说实话,一个人在世上所需要的并不是很多,我现在不缺吃不缺穿,出门我不想走路就可以打的,担心没饭吃那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没钱当然不行,但是如果我现在银行里放几千万,我不知道要拿它来干啥。我对爱人讲:钱花掉才有用,否则就跟我扔掉的废纸一样。
记者:您夫人说您喜欢看中国队与外国队的比赛,并且您的民族感情比较强烈。
李世鹤:我什么比赛都喜欢看,只是没有时间。作为一个中国人哪能没有民族感情?中国是有缺点,但欧美国家我也走得多了,去过之后我感到很满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终于给了我们为自己国家干事的机会。
记者:您经历过文革的冲击,为什么当时还选择回国?
李世鹤:我当然要回国了。我可以给你讲得很坦率。
一、热爱自己的国家是最起码的准则。要对自己国家有基本认识,在文革中我只是运气不好倒霉而已,我这个性格是迟早要倒霉的。而且,我们那批出去的人基本上都回来了。原因很简单,没有邓小平、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不可能出去,我们不能给邓小平抹黑。而且种族歧视在国外非常多。比尔.盖茨能成功,一个中国人不是绝对没有机会、但是很难,毕竟不是在自己的祖国。
二、为了我们当时四所的党委书记王善士,我也要回来。他是1945年投奔延安的老干部,1978年他官复原职以后,让我参加出国人员考试。结果我考过以后,他老先生就坐着所里唯一的一辆破吉普车跑到省委,从早晨一直坐到晚上,这样把四所的“反革命”一下子都解放了。他对我说:研究所希望你学成以后回来。再加上我有家庭,有父母、岳父母,我不可能都把他们接过去当美国公民,他们也不会去。
记者:有人认为您之所以不离开大唐(四所的上级单位),就是因为王善士、要回报四所,您的看法呢?
李世鹤:当时回来,更多想到的是国家,想到要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至于我不离开大唐,原因很多。回来后,部里、院里对我抱有很大希望,一些领导也给予过很多支持。虽然也因不满于旧体制的束缚,我几次辞去“官职”、还一度离开过,但我一直没有把事情看死,总希望工作了一辈子的研究院能够办好。实际上它也不是一无是处。
记者:有人说您这项技术如果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国外获得成功,会很了不得,个人会比现在得到的多得多。
李世鹤:在国外生活太容易了,我何必要发明这些东西。我拿着二十年前的本事,混个十万八万美元年薪很容易。我不是不想混吗,才干这件事。而且,如果我在外国公司有了这个新技术,我凭什么要贡献给所在公司?我可以自己办一个公司。
记者:很多业外人士知道大唐提出了我国的标准,却不知道您与它的关系,对此您怎么看?
李世鹤:这是很正常的,企业排在最前面。如果是外国人,更要讲这是中国的技术;如果在月球上,则会看到它是地球的技术。
当我六十岁的时候,终于做了一件对中国有贡献的事情,这五六年可能是我一辈子最玩命的时候
记者:您今年已经到六十岁了,决定退休吗?
李世鹤:对。
记者:退休后有什么打算?
李世鹤:我打算做一个自由人。可能有很多企业想让我当顾问,但是我跟他们讲明了钱不要多付,我也不占你们的管理职位,不在你们那儿按点上班,但是我所知道的会全部无偿贡献给你;但也休想让我为你保密,我跟你讲的技术对别的企业也照样讲。但外企请我,我是绝对不去的。
记者:您退休后,这项技术归谁?
李世鹤:技术专利都是大唐的,现在做的一切包括外面挂那么多专利,都是大唐的,靠这些它可以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
记者:在其中您占多少份额?
李世鹤:没有。我从来没想过要靠自己的这些东西来敲诈谁一下。
记者:TD-SCDMA应该说就像自己带大的孩子,很容易舍不得。您怎么没有这种情绪?
李世鹤:我也舍不得,我没说不管它。但是我认为不应该占着这个位置,应该让年轻人起来。你只要不退休,年轻人就坐不到这个位置上,即使他们完全有能力。现在有好多工作是让他们在做,从去年夏天开始我已经放得差不多了。
记者:这么多年走过来,您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李世鹤:当我六十岁的时候,终于做了一件对中国有贡献的事情,这五六年可能是我一辈子最玩命的时候,1994年到北京以后,我几乎没有时间休息。
记者:您有没有感到遗憾的事情?
李世鹤:没什么。可以得到了一个机会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做成一件事情,足矣。 你不可能做成两件、三件。我经常跟我爱人讲:一定要满足,人一旦满足后就会感到自己很舒服。
记者:您在1987年的时候曾说过自己有两个目标:一 是看到我国落后的通信状况得到改变,并在这个过程中,为通信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另一个是成为国际上一个一流的专家。您的目标实现了吗?
李世鹤:希望能够将现在几乎被外国人占光了的移动通信市场,抢回几个百分点,做得好能抢回一二十个百分点,这在两三年以后就会实现。至于我个人,我认为现在不比老外差。
记者:中国通信产业根本性的好转还需几年?
李世鹤:我估计还得十年。 (本报记者 朱 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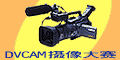
![]() 版权所有 四通利方 新浪网
版权所有 四通利方 新浪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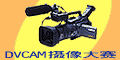
![]() 版权所有 四通利方 新浪网
版权所有 四通利方 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