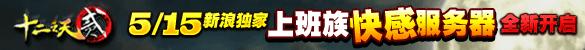华夏地理:澳大利亚在苦旱中挣扎

澳大利亚在苦旱中挣扎
撰文:罗伯特·德雷珀 ROBERT DRAPER
摄影:埃米·滕辛 AMY TOENSING
翻译:王丽蕊
气候毫不留情地背叛了他。
澳大利亚东南部某处的一条路旁,有个男人坐在熄了火的皮卡汽车里,思量着他从多种意义上变得干涸的生活。两个最明显的方面一目了然。就在卡车的近旁,他的奶牛正啃食路边的青草。谢天谢地,这些小母牛都很健康,但总共只有70头。五年前,他拥有差不多500头奶牛。让奶牛在公共道路旁吃草,“严格来说这并不合法”,男人承认,但除此之外他还能怎么办?他的牧场寸草不生,土地如今成了一片灌木杂生的沙漠,最轻的风吹过也会掀起一道沙尘飞扬的屏障。他再也买不起谷物饲料,这在另一些反映他生活窘况的参照物中表露无遗——他的银行账户报表就显示在搁在汽车仪表板上的笔记本电脑中。这个男人过去既没发过财,可也没受过穷,如今却已经欠下了数十万美元的债务。他透过挡风玻璃凝视着牛群,那是他仅剩的收入来源。
男人名叫马尔科姆·阿德林顿,在他52岁的生涯中,有36年都以饲养奶牛为业,每天清晨5点起床挤当天的第一拨牛奶成了惯例。在并不久远的过去,阿德林顿还常期盼着一项叫做“奶牛场漫步”的典礼。州里的农业官员会把当地奶农召集到一起,参观模范牧场——这荣誉通常都归阿德林顿所有。他的牧场位于新南威尔士州巴勒姆城的郊外,面积不大,那时却经营得红红火火。奶农们在那里仔细打量阿德林顿用谷物喂养的奶牛。他们会问他如何令牧场绿草茵茵——他喜欢什么品种的草籽,用什么肥料,阿德林顿也十分乐于与人分享他的秘诀,他知道换了请教的人是他,同行们一样会倾囊相授。这就是农场主的精神,也是澳大利亚的精神。一个人尽可以自由地尝试、慷慨地传授他的技术,不动声色地坚信自己的努力和才智仍会脱颖而出。
如今,阿德林顿说道:“那些都是旱灾发生前的事儿了。”十年前,阿德林顿雇有五名帮工,“现在只剩我们夫妻俩了。”他说,“最近三年我们基本没水可用,就被这个逼上了绝路。”
然而不远处就有水。在距离阿德林顿停车处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就能看到有水从主路下潺潺流过。它就是“南部主水道”,从澳大利亚富于传奇色彩的墨累河引出的一条灌溉渠,与达令河及其他一些水道构成了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的水源,并供应着整个澳大利亚65%的农业用水。阿德林顿持有一份许可证,每年能从墨累-达令水系取得约100万立方米的水。问题是,有限的水源被许给了太多使用者:阿德莱德市、大型农场企业,还有受保护的湿地。因此,过去三年里,新南威尔士政府几乎完全禁止阿德林顿从这里取水。他仍旧要为自己的用水配额缴费,却一滴水也用不了,除非旱情结束。阿德莱德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极为愤怒,同时,他正在低价清出心爱的奶牛。
“让人动不动就灰心丧气。”他以冷静平淡的嗓音说道,“我对自己发问,为什么干上了这一行?”马尔科姆•阿德林顿过去很少质疑过自己,近来他就像变了个人。干旱夺走的不止是他的土地,他发现自己不断与妻子玛丽安娜争吵,对孩子大呼小叫。他付不起汽油钱,不能像以前一样开车带玛丽安娜进城。随着其他农场纷纷关门大吉,现在能和他儿子一同玩耍的男孩,最近的也住在15公里之外。
阿德林顿已经开始出售自家的土地。“到现在连个来看地的买家都没有。”他说。这显然是个无奈的选择,阿德林顿家从来没有人愿意这么做。但他的父亲或祖父何曾遇到过这该死的七年大旱?
自阿德林顿印象中的最后一场“奶牛场漫步”以来,已过了炎热干涸的三年。此间只有一系列为鼓舞民心而举办的活动,它们都有着积极向上的名目,比如“战胜困难时刻”,“男子三项全能”,或是“纵情欢乐日”——这正是阿德林顿的妻子今天要参加的活动,农场女性能在这里享受免费的按摩、美甲和发型设计。一位治理旱情的工作人员会给女人们沏上茶,鼓励她们交流想法。她们从不同侧面讲述着同一个故事。
“两年了,颗粒无收。”
“家里的农场快经营不下去了。”
“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羊都卖了——我们养了20年的漂亮家伙们。”
“我真受不了每天夜里躺在床上,听着牛群饿得惨叫。”
然而最凄惨的会面是在公众视线之外的。其中的一次发生在斯旺希尔附近一座简陋的农舍里。一位在政府供职的农乡财政顾问坐在厨房的餐桌上,建议一名中年果农和他妻子宣布破产——他们的债务已经超过了农场的价值,一场冰雹又刚刚毁掉了他们的作物。
农民握着妻子的手,泪水夺眶而出,艰难地从嘴里挤出一句话:“确实没什么好让我继续撑下去的了。”
农妇说她每隔几个钟头就得去田里看看,确认她丈夫没一枪打穿自己的脑袋,倒在果园里。会面结束后,财政顾问将他们的名字列入了自杀高危监控对象的名单。
回头再看巴勒姆,马尔科姆·阿德林顿独自坐在卡车里,哪儿也去不了。看着自己的奶牛越来越少,看着草场退化成灌木荒漠。他所能做的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有人类定居的最干旱的大陆,水源匮乏到了危险的地步。除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之外,它的水危机是错综复杂的。尽管澳大利亚人以往每隔些年就会经受一次旱灾,但目前这场长达七年的干旱,却是该国有文字记载的117年历史中破坏性最强的一次。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异常的降雨模式是人类造成气候变化的不祥之兆。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变暖已经让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程度越来越严重。有一件事看来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澳大利亚环境科学家蒂姆·凯利所说:“过去15年中,气温升高了0.75摄氏度,我们这里有更多的水被蒸发掉了。这就是气候变化。”
澳大利亚花了些时候才认清这个现实。毕竟,当初改造这个国家的是一批不畏穷山恶水的乐观主义者,生活在全球最贫瘠的土地上也不以为意。澳大利亚科学家蒂姆·弗兰纳里称之为“低养分生态系统”,土壤已经变得老旧而贫瘠,因为在过去的百万年当中,土地没有受过冰川的搅动。墨累-达令流域是一块面积相当于西班牙与法国之和的半干旱平原,远途而来的欧洲人被19世纪中期连年多雨的现象蒙蔽,还以为自己发现了一座近代伊甸园。这些定居者按照故国的开拓习惯,伐倒大约150亿棵树木,并没意识到毁掉适应干旱环境的植被,破坏原本稳固的水循环体系会有什么后果。这些新澳大利亚人引进了绵羊、牛和各种需要大量灌溉的农作物,与当地的沙漠生态系统全然相悖。人们为增加产量无休无止地耕作,进一步加剧了土壤的退化。
有条河流因此成了当地的生命线。长2530公里的墨累河富有神秘学上的重要意义,象征着无限的可能性。它那由回水湖、赤桉树、墨累鳕鱼和黑天鹅构成的生态网同内陆地区一样,体现着澳大利亚的风骨。从发自澳大利亚阿尔卑斯山脉的源头,到汇入印度洋的入海口,墨累河的涓涓细流向西北一路蜿蜒前行,在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之间划出一条长长的分界线,同时融汇马兰比吉河与达令河的水流,然后进入南澳大利亚州的半干旱灌木区,最终在因康特湾奔流入海。它似乎有意流淌得不紧不慢,甚至变化无常,更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
为了开发土地,澳大利亚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令墨累河转向。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对这条河进行了“机械化”,建起大量水闸及拦河坝,从而使河水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墨累-达令流域依赖灌溉的农民。结果,“河流出现了异常。”澳大利亚前国家水资源部长马尔科姆·特恩布尔说,“由于受到干预,水位在本该下降的时候上涨,在本该上涨的时候又反而下降。”人为的操控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后果。灌溉导致土壤含盐量急剧增加,进而破坏了湿地,令大片土地不再适于耕种。